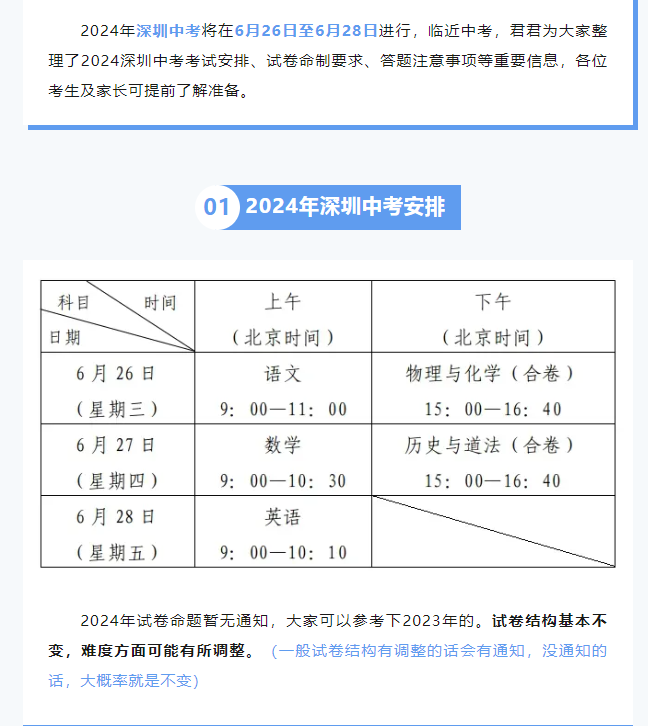我已经活了400多岁了。
我是地坛,400多年的风风雨雨,剥蚀了我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,淡褪了门壁上耀眼的朱红,坍颓了一段段高墙。游人一茬又一茬地来观看我,但我感觉无人能真的懂我。
一个下午,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变得愈加大,愈加红,沉静的光芒弥漫着整个公园。忽然,一个残疾的年轻人在宁静的园中出现了。他摇着轮椅进去,我的内心突然一颤,仿佛是一种宿命,我了解,一个最懂我的人出目前我的生命中了。
相处一段时间后,我了解了他叫史铁生,由于残疾,过去产生过轻生的念头。我伴他在树下徘徊,看一些孩童在温暖的阳光下嬉戏。我对他说:孩子,这不是别的,这是你的罪孽与福祉。他仿佛是听到了,四肢猛地一震,在园中扶椅徘徊,不时沉静地思索。在一片朦胧的夜色中,他思索着归去。
后来,他便常常来我这里,在阳光下,抑或在雨后,与我无言地对话。春季是树尖上的呼喊,夏季是呼喊中的细雨,秋季是细雨中的土地,冬季是干净的土地上的一只孤零的烟斗,在一抹生的期望中,他了解了我的意思要懂得感恩我们的命。
有时,我还与他一同聆听祭坛深处的唢呐声。在苍茫的夜色中,坦坦荡荡,独对苍天,只听得唢呐声在星光寥寥的夜空下低吟高唱,时而悲怆,时而欢快,时而缠绵,时而苍凉。这个时候,他便从这喷呐声中了解了我的思想: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,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,在参悟死亡中,他了解何为永恒;在时光静寂之处,他知道了何为无穷。
就如此,在无数个日日夜夜里,他在无言中领会着我的心绪,在一片沉静中聆听我的声音,大家一同赞美生命的欢唱,一同领悟和考虑生命的永恒。
而今斯人已逝,但在我的心中,他这个残缺的生命,已变成我永恒的知己。由于只有他,最为懂我。